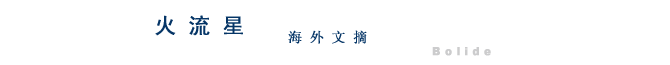
|
||
|
爱因斯坦的沉默
|
||
|
Anil Ananthaswamy 文 Shea 编译 |
||
|
聆听时空的孱弱细语需要一个比它自身更安静的地方。 黄昏已降临在美国华盛顿州的响尾蛇山。一弯新月悬挂在山脊之上,透过缕缕的薄卷云,金星闪耀出明亮的光芒。当地亚基马县的人们称它是“水上的土地”,这是因为它曾在肆虐于其下方平原的洪水中屹立不倒。 如今,这一高1000米的山脊则俯视着下面为山艾树所覆盖的寂静草原。这一寂静的背后其实隐藏着秘密。就在附近长大的桂冠诗人凯瑟琳·弗莱尼肯(Kathleen Flenniken)写道:“......这座山的褶皱和阴影,伴随着星星和春天的绿色,掩盖了隐藏在地下发射井中的导弹和50年前原子弹的废弃物。” 1942年12月,美军从响尾蛇山上方飞过,他们称之为完美的“隔离荒地”,可以在那里生产制造原子弹所必需的钚。投放到长崎的原子弹“胖子”其核心就由这里的汉福德核设施制造。在冷战的巅峰期,这里有9座核反应堆和5个核燃料加工厂。 今天再飞过响尾蛇山则会看到两根极为不同且神秘的混凝土管。它们长几千米,直径几米,在荒凉的平原上以直角的形状排布。 每到夜晚,汉福德过往的阴魂就会再次聚集,这里也似乎更加的寂静。但对于在这些混凝土管子里正在做的事情而言,普通的寂静远非足够。 在过去一个世纪的物理学中,爱因斯坦的影子依稀可见。虽然他反对原子弹,但汉福德核设施却仰仗着他E=mc2的方程,它描述了质量是如何释放出能量的。 质能等价源于爱因斯坦1905年提出的狭义相对论。正是它把光速c确定为了宇宙速度的最终上限,并开始撼动长久以来时间和空间绝对、不变且彼此独立的观念。 不过狭义相对论只是一道开胃菜。1915年爱因斯坦提出了广义相对论,这一杰作重新诠释了物质、引力以及宇宙事件所发生的舞台——时空——之间的完整联系。 在爱因斯坦的宇宙中,引力已不再遵从两个多世纪前牛顿所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它也不再是一个物体可以瞬间施加到另一个物体之上的神奇作用力。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大质量的物体会扭曲其周围的时空,就像一个铁球会使得一张橡皮膜发生凹陷一样。由太阳在其周围时空中所产生的这一扭曲使得地球和其他行星围绕其公转;地球对其周围时空的扭曲则使得我们的双脚可以牢牢地固定在地面上。引力只是时空的曲率而已。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广义相对论的预言一次又一次的通过了检验。从英国天文学家亚瑟·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在1919年日全食时证明太阳会使得经过它的光线发生弯曲,到现代对星系团弯曲更遥远类星体所发出光线的测量,广义相对论还从来没有失过手。但奇怪的是,即使过了这么多年,它的核心预言却至今还没有被直接验证。 正是爱因斯坦本人第一个开启了这场冒险。在一篇题为《关于引力波》(Über Gravitationswellen)的论文中,他提出,如果物体能弯曲时空,那么运动的物体也许就能使之振荡,从而产生波。至少广义相对论的方程表明,这似乎是可能的:爱因斯坦证明一个旋转的椭球体——类似一个非常巨大的橄榄球——可以在宇宙的时空结构中产生涟漪。 但他并不太确信这一点。差不多20年后,和年轻的同事内森·罗森(Nathan Rosen)一起,他把一篇名为《引力波是否存在?》的论文投稿到了《物理学评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一个谨慎的“不”字。但这篇论文从未正式发表,该杂志的编辑约翰·泰特(John Tate)把它发给了一个匿名的审稿人。感觉受到了冒犯,爱因斯坦撤回了稿件。他似乎不乐于被同行评审。 但是,这也给了他时间去发现计算中的错误,进而在1937年正式刊载于《富兰克林研究所杂志》之前更正了他的预言。爱因斯坦自己最终也认可时空结构中存在涟漪,而且它们会荡漾于整个宇宙之中。 弗农·桑德伯格(Vernon Sandberg)自豪地指着他白板一角照片上的爱因斯坦说:“这是位大师。”这是1927年爱因斯坦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索尔维会议时所拍摄的著名照片。用今天的眼光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坐在前排正中央,周围全是新兴的量子力学家们:玻尔,海森堡,普朗克,薛定谔。 曾经受训成为一个理论物理学家,但桑德伯格现在却是位于汉福德的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众多实验物理学家中的一员,该天文台就座落于旧的核设施旁。70年代初期,桑德伯格爱上了爱因斯坦关于空间和时间的想法。正是在那时,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物理学家约瑟夫·韦伯(Joseph Weber)声称第一次探测到了引力波。 韦伯的探测器现在是博物馆中的展品。一个被陈列在美国盛顿特区的史密森学会,另一个则矗立在LIGO汉福德主楼入口的大堂里。这两个加工精美的铝制巨型圆柱体曾用钢丝分别悬挂在相距约1,000千米的马里兰大学校园和位于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附近的阿贡国家实验室里。1969年,韦伯报告称,这两个圆柱体先后以81天的周期发生了17次振荡。由于地震、声波或电磁波触发这一突然共振的可能性很低,于是他在《物理学评论快报》的论文中写道:“这是引力辐射已经被发现的绝佳证据。”  [图片说明]: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LIGO。版权:LIGO。 他有充足的理由来如此的乐观。根据广义相对论的训诫,引力波应该无处不在。从大质量恒星坍缩爆炸成超新星,到中子星和黑洞间逐渐靠近和并合,再到大爆炸之后不久时空的剧烈涨落,宇宙中的许多爆发性事件都应该会产生以光速传播的引力波。 然而,今天的共识是韦伯并没有探测到引力波。若真如他所说,为了使得这两个圆柱体发生振荡,在我们周围的宇宙中必须充满极强的引力波源,但现实似乎并非如此。 直到今天,唯一被广为接受的引力波存在证据仍是间接的。1974年,天体物理学家约瑟夫·泰勒(Joseph Taylor)和拉塞尔·赫尔斯(Russell Hulse)发现了一个距离我们21,000光年远的双星系统。其中至少有一个天体是高速自转的中子星——脉冲星。对该系统的观测表明,它们彼此绕转着相互靠近的速度正如因辐射引力波损失轨道能量所引起的。 虽然2014年3月又迎来了引力波的另一个间接证据——南极BICEP2实验的天文学家宣布在大爆炸的余辉微波背景辐射中发现了原初引力波所留下的印迹——但30多年来我们依然止步不前。 对于还没有直接探测到引力波,桑德伯格给了一个解释。他说:“时空真的真的很坚硬。”比钻石还要硬上十万亿亿倍,所以即使是极为剧烈的宇宙事件也只能在其中产生弱得可怜的引力波。由两颗质量分别为1.4个太阳质量的中子星在它们死亡探戈中所发出的引力波——被引力波天文学家们用作标杆——会拉伸或挤压我们到比邻星之间4.3光年的距离,但其幅度还不到人头发丝粗细的一半。 如果我们能建造一架从地球延伸到比邻星的仪器,那这一效应是可以被明晰测量的。但残酷的现实是,LIGO很可能是我们目前最好的探测工具了。 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也建造了几架类似的激光干涉仪来探测引力波,但LIGO是它们中最大的。它有着两条几乎完全一样的激光干涉臂,每条都长4千米。它的一条激光臂从其主楼向响尾蛇山伸出,另一条则与其成直角指向汉福德核设施的退役反应堆。 每一条臂都包含一根钢制外壳的真空管,从一束激光中被分出的一半激光会被置于其远端的镜子来回反射。返回主楼之后,这半束的激光会与另外半束在另一条臂中传播的激光重新汇合。 因路经的引力波所造成的时空扰动而引起的任何臂长变化都会改变两束激光汇合后所产生的明暗相交的干涉条纹。引力波会在挤压一个方向上挤压空间,而同时又在另一个方向上拉伸它,这使得以直角张开其探测臂的LIGO的灵敏度得以翻倍:当引力波穿过它时,其一条干涉臂会先变长再变短,而另一条臂则相反会先变短再变长。 但别忘了这一效应微乎其微的影响。标准的引力波预计只会使得LIGO的臂长拉伸或者收缩10-19米,仅相当于质子直径的万分之一。 如果你只在一个地方看到了这么微小的运动,那你永远不也能确定它是引力波信号还是背景的噪声,所以就像韦伯的共振棒探测器,汉福德的激光干涉仪仅是LIGO的两个成员之一。另一架完全相同的干涉仪则位于3000千米之外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利文斯顿的河口。如果以10个毫秒的间隔先后在这两个探测器中看到了同一信号(引力波在这两者间传播所需的时间),那你才能说下一步如何如何。 或者,即便如此也还是不行:为了要测量出最微小的变化,任何可能的干扰,哪怕最微小的噪声,都必须被抑制。唯有绝对的寂静才行。 当我抵达汉福德时,正值冬天的第一场寒流来袭。当我行驶在240号高速公路上时,响尾蛇山在我的左侧若隐若现。沿途流淌着的亚基马河,其仍然温暖的表层水正在蒸发和冷凝,看上去就像热气腾腾的温泉。河沿岸的灌木和树木上覆盖着细霜,宛如寂静冬日的风景画。 汉福德核设施的一些地方是地球上污染最严重的地点之一,其地下储罐内装有含钚、铀、碱和酸的废弃物。有笑话说,这个核设施周围游荡的兔子都具有放射性。不过,对于LIGO来说,最大问题是颠簸在240号高速公路上的18轮清运卡车。“这会对地面产生很强的低频撞击,”迈克·兰德里(Mike Landry)说。 空气和大地的振荡都是有可能让LIGO“失锁”的噪音。兰德里常常会提到“失锁”这个词,他是一个体魄强健但说话轻声细语的加拿大物理学家,自2000年来到汉福德就并从未离开。在为第一代LIGO工作了十年之后,他目前正负责监督对LIGO的升级工作,计划在2014年底完工。和在LIGO工作的几乎所有人一样,他每天都在和噪声打交道。 为了提高探测器的灵敏度,光要沿着干涉臂被多次地来回反射。在升级后的“高级LIGO”中,目的是要反射100次,这样可以使得4千米的臂长等效成400千米长。为了做到这一点,反射镜必须严格保持静止。 然而,现实是这仅仅是字面上的。问题始于地球不断的地震。再就是因月球的轨道运动对地表所造成的扭曲。每过12个小时,它会使得LIGO的臂长变化约十分之一个毫米——看似是个微小的量,但相比于经过的引力波所能产生的效应而言却极为巨大。不过,这一噪声源至少是可预测的,能够通过连续调节注入干涉仪的激光频率以及反射镜之间的距离来补偿潮汐的影响。 反射镜本身则是用粗线差不多1毫米的石英玻璃线悬挂起来的,以此来尽可能地隔绝来自地面的干扰。此外,叠加起来的叶片弹簧和单摆则有助于过滤掉高频噪声。伺服电机会俯仰、转动和偏转这个5吨重的装置来抵御低频的地面振动。这是从利文斯顿LIGO早期运转中所获得的深刻教训,在其周围森林中伐木场工作的重型机械所发出的的低频声浪会产生持续且不可预言的噪声。“一些倒下的树木还会产生连续刺耳的噪声,”兰德里说。 他列了一份长长的意料之外和刺激性噪声的清单。汉福德LIGO中出现的神秘而不规则的多普勒频移声学噪声与大约20千米之外里奇兰机场飞机的起降时间相吻合。另外,每年春季每过几晚就会有一个神秘的噪声突然增强然后又慢慢退去——这是由于附近的水坝释放冰雪融水而产生的隆隆声。有时候,噪声的来源既非来自本地,也不无明显特征。“当LIGO在运转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北冰洋上的风暴,”桑德伯格说,“当这些风暴在西雅图沿岸登陆时,我们可以准确无误地看到它们。” 对于LIGO来说,汉福德冬天的寂静只是表象。我从来没见过LIGO的反射镜,每一面都由高度抛光的、明晃晃的的石英玻璃制成,呈圆盘状,重40千克。“如果围绕它们移动,你会看到泛出的漂亮颜色,”桑德伯格说,“非常的华丽。” 把发射镜打磨到这一状态绝非易事。美国洛杉矶的一家公司首先对其表面进行抛光,使之透明。在旧金山附近,再对其材质进行逐个分子地蚀刻,在一个硅原子直径的误差范围内使之满足所需的曲率。从那里,它们被空运到法国,在那里对其表面进行最终的镀膜,以此来限制镜面分子在已知频率的热运动。如果它们一起振动起来的话,就会像敲击水晶酒杯一样——是另一种需要考虑的噪声源。 “那么我们用它们来做什么呢?”桑德伯格说,“我们把它们放入没有人会再次看到它们的真空管中。”LIGO的反射镜和激光束被放置在了近地轨道之下最大的超高真空腔内。在这个约1万立方米的空腔中,它确保了激光束在来回反射的过程不会因为有遗留的任何分子而发生偏折。即便是靠近这个真空腔的边缘也要把我的鞋子伸进一个转动的清洁器,去除上面的污垢,然后穿上鞋套,带上头套,以此来更好地控制住我身上不守规矩的分子。 “我们的宝贵资产,”桑德伯格说,“正是空无一物的真空。” 在狂野西部的传说中,风滚草会被吹到空无一物的地方。在汉福德,它们经常会被吹过整个荒原,堆积在LIGO的混凝土臂上,制造火灾隐患。除了噪声之外,清理风滚草并把它们像干草一样打包也是常事。 理论上讲,升级前的LIGO已灵敏到可以探测6500万光年之外的标准源所发出的引力波。在十年的运转和一无所获之后,我们现在至少可以给引力波有多强设定一个上限。(虽然就在我们附近,但泰勒和赫尔斯所发现的双星绕转速度过慢,其辐射出引力波信号的频率远远低于LIGO可探测的阈值。仅在约3亿年后这两个天体最终并合前,它所发出的引力波才能被目前地球上的探测器捕捉到。) 将于今年投入使用的高级LIGO能将这一探测距离扩大十倍,由此其可搜索的空间体积则扩大了一千倍——这是一次巨大的飞跃。从地震干扰到单个分子的热运动,过去十年对所有已知的经典噪声源进行了研究并想办法对它们进行了抑制。这些噪声会使得反射镜发生运动,模仿或掩盖掉引力波信号。兰德里很有信心地说,如果确有引力波通过升级后的LIGO,它一定会探测到。“我们不想再进一步给出更低的上限了。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做出发现。” 但量子力学却说,事情不会这么简单。爱因斯坦从来都不喜欢量子理论。即使在索尔维会议的照片中他看似量子力学的坚定支持者,他反对量子力学用概率来描述现实的观点。随着时间,这种情绪只增不减。爱因斯坦曾说:“上帝不掷骰子。” 在这个问题上,爱因斯坦似乎错了。量子世界满是掷骰子众神。我们与其之间联系的核心是一个爱因斯坦与玻尔争论了数十年的原理:量子不确定性。 根据测不准原理,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同时精确测定量子世界中成对出现的两个属性。位置和动量构成这样一对属性:我们知道一个量子粒子的位置越精确,我们对它速度的了解就越模糊。能量和时间则是另一对这样的属性。这对于LIGO来说,听起来很可怕,因为精确知道光子打到反射镜上的时间和能量是探测引力波的关键。 更奇怪的是,不确定性噪声不仅仅会扰乱光子,还会影响真空。真正用来检测引力波的是由LIGO两束激光重新汇合并干涉之后所形成的明暗条纹。当没有引力波入射的时候,它完全是暗的。但量子不确定性认为,即使在黑暗中也会有光。在空无一物的真空中,时空的量子涨落会产生光子,这会对光信号产生微妙的影响,干扰引力波的探测信号。 因此,即便经典世界中的每一个噪声源都已被识别和解释了,但搜寻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缺失一环的努力也许会最终受限于他本人不乐意接受的量子理论。“我觉得这多少有一点命运扭转的感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家纳吉斯·马瓦尔瓦拉(Nergis Mavalvala)说,“如果你愿意,这也算是有点戏剧性了。” 80年代初,物理学家卡尔顿·凯夫斯(Carlton Caves)最早意识到了这种古怪量子噪声的存在,并想出了消除它的办法。不确定性不会限制我们对某个量的测量,但会制约对一对观测量的了解,因此它也有一定的弹性。例如,你要测量一个光子的到达时间,你可以通过尽量少地了解它的能量进而来限制对时间测量的不确定性。 这是完全可行的:“压缩”一个光子,使得其不确定性集中到它成对特性中的一个,由此可以几乎不受噪声干扰地测量另一个。更奇怪的是,至少在理论上,你可以把对光子的这一操作用到真空上。通过压缩器来逐渐减少光的流量直至其消失,压缩态光场就会在另一端出现,由此可以以如你所希望的方式来操纵真空的特性。“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戴维·麦克莱兰(David McClelland)说,“这几乎就像魔术;它是真空,但又全非如此。”几年前,他的团队制造了一个光压缩器。通过在光子探测器上将光压缩到真空,他们把探测器的固有噪声降低到了其自然水平以下。 “这都神了,不是吗?”马瓦尔瓦拉说。与她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希拉·德怀尔(Sheila Dwyer)一起,他们把压缩真空应用于LIGO干涉仪,也观测到了其量子噪声的下降。LIGO探测器变得比真空还要寂静。 最快到2017年,压缩光场会全面应用于LIGO。之后,当周围环境比寂静还要安静之时,我们的耳朵可能最终会聆听到时空的引力私语。对于由此可以获得什么,桑德伯格略加思索。他说:“我们将能够看到发生在黑洞事件视界上的事情,我们也将能看到中子星爆炸的内部细节。”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无法想到更有意思的东西。“对于通过LIGO我们到底能看到些什么,能用它来干些什么,我是个缺乏想象力的人,在这一点上其他人也是一样,”他说,“但这真的令人兴奋。它代表了100年来我们对物质、能量以及距离和空间基本概念间最深层关系的最艰苦卓绝的探究。我想不出比这更深入和更深刻的了。” 美国原住民所知的洪水可能永远不会再重返汉福德平原。但也许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探测到另一种不同的波路经此地。麦克莱兰说,首次探测到引力波将会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这就像第一次能听见周遭的宇宙一样。” |
||
|
[New Scientist 2014年4月12日]
|
||
2001-2016 火流星工作组制作

本文遵循“创作共用约定”之“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演绎”3.0约定
任何意见和建议请致电: